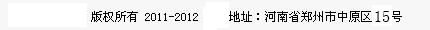纵观河套灌区的发展历程,就是一部开发利用水资源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奋斗史。这期间,无数的治水先驱和水利工作者将他们的勤劳、智慧和汗水,洒在了这片沃土上,为河套灌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66年前的那个冬天,河套人民开始了人工开挖总干渠的“战役”。历经近10年的时间,才完成了黄河流域最大的灌溉渠道的开挖。
为了寻找这段珍贵的往事,近日,《追寻河套记忆·聆听水利故事》专访组前往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宏光村红圪卜组,与三位“80”后老人一起回忆那段开挖总干渠的青春岁月。
开挖总干渠施工场景图源自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
“挖过总干渠的人,年龄最小也得80了。”年出生的张五银,是三位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位。总干渠开始动工那一年他只有15岁,算得上是工地上年龄最小的一批了。当时,村里的劳动力全都参与了总干渠的开挖,年出生的迭罕达和年出生的陈为忠也是其中的参与者。三位老人见证并参与了河套灌区最重要的建设时期。
“还没有总干渠的时候,我每年春天都得去黄河边捞渠口。挖通引水渠,才能浇上地。”陈为忠老人说。过去的黄河在河套地区有两条支流,一条是沿着阴山顺流而下的北河,是当时黄河的主河道,另一条南河就是现在的黄河,过去只是一条支流。年左右,黄河北河受到乌兰布和沙漠的不断侵袭,最终断流,所有河水涌入南河,南河成为主流,形成了如今黄河的格局。河套地区地形西南高、东北低,这样的地形条件使得黄河成为了整个套区的最高点。晚清时期,当地地商就利用这一地形优势在黄河上直接开口挖渠,黄河水通过地形高度差就可以自流进行灌溉。但黄河河道每年都在摆动,这就导致渠道口不断被冲刷、毁坏。为了灌溉用水,虽然春耕时节是农民最忙的时候,也不得不抽调大批劳动力,在冰水中疏浚引水渠口。这就是老人口中提到的“捞渠口”。
每年疏通引水渠都是一项大工程,陈为忠老人回忆说:“当时没有水靴,就站在冰水里施工,条件非常艰苦。长济、通济、义和、塔布这几条渠都是从这条引水渠引水,这个引水渠很重要,所以受点儿苦咱也得干。”乌拉特前旗、五原县组织农民自发疏通渠口,当时两个县分别在河道两侧制作了埽棒,埽棒中间用铁丝拉住,绑在柱子上,防止埽棒被黄河水冲走。老人起身比划着说:“这个埽棒得有一人高。”疏通了引水渠,黄河水才能顺利进入渠道,但是在汛期,渠堤薄弱地段,时常会发生决口。水大淹、水小旱,生产用水还是得不到保障。
总干渠工地图源自巴彦淖尔市档案馆
“当时国家号召我们去挖总干渠的时候,很少有人有怨言,大家都知道,挖通了总干渠才能好好种地。我们家兄弟四个轮流去挖。”张五银老人继续说。“我们家弟兄两个也是。”迭罕达老人补充道。“那时候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都去挖总干渠。”陈为忠老人继续说,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,每天只能吃点儿糜米饭,根本吃不上菜,偶尔吃点酸粥就算是改善生活了。”迭罕达老人说:“吃咋都能凑乎,能吃饱就行,主要是住的艰苦,住的是‘个桶房’”。迭罕达老人口中的“个桶房”是什么呢?“个桶”是巴彦淖尔方言,形容桶状的物品,房子怎么会是桶状的?老人接着介绍,原来由于远离村庄,缺少住所,工地上就以大队为单位,组织盖了一些低矮的临时土坯房,这些房子房顶还没有一个成年人高,也没有炕,里面弄个泥炉子就是唯一的取暖设备,几十个人每天就挤在一起睡地上。
那时候不仅生活条件艰苦,寒冬施工也异常艰难。规划渠道内全都是冻土,根本挖不动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炸开,每天晚上都会有专人炸冻土,但冻土块很大,原本用来装土的箩头根本装不下,于是,大家就开始自己制作工具。当时没有现在的条件,大家就弄了一个简易搬运工具,虽然简单,但是运量很大。人们用铁丝把杠子绑起来做成搬运工具,一次能放上一两百斤重的冻土块,然后抬出去。剩下的冻土,再用铁钎子顶着,用铁锤锤成小块儿,再用箩头担出去。“当时我们挖的那一段总干渠要求开口30米,加上20多米的旱台,两个人根本上不去,实在是太重了,需要几个人轮流接担,才能顺利担出去。”迭罕达老人说。
比起担土这样的体力活,锤土、装土会相对轻松一点儿。陈为忠老人说:“当时每个工种都是轮流干的,担一会儿土,装一会儿土。”张五银老人接着说:“其实装土也不轻松,一锹下去就是二三十公分高的土块,大点儿的土块得有五六十斤重。那时候大家在工地上没人闹意见,都是一心想要尽快完成任务。干活儿哪有不累的,累点儿、苦点儿才能干出活儿。过去没有手套,寒冬腊月,手上冻的都是血裂子,冻得不行就搓搓手,继续干。”
开挖总干渠施工场景图源自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
为了尽快完工,那时候不仅在农闲的冬季施工,迭罕达老人回忆,他当时先去挖了一冬天渠,回家过完年又赶去工地。当时河套地区的地下水位较高,在挖总干渠的过程中不时都会挖出水来。冬天要在冰水里劳动,春天就是在泥里挖渠。泥土沾在箩头上倒都倒不出去,干一会儿就得清理一次箩头。“我记得可清楚了,等挖完渠,再回家时麦子都已经上来了,我带去工地的箩头也用烂了。当时的家长们,也很放心孩子们去挖渠,在工地他们不仅能有口饭吃,还能挣点儿补助。”张五银老人笑着说。
当时虽然艰苦,但想想以后的好日子,大家是有盼头的。“那会儿很少有人抱怨,大家都明白,今天的辛苦是为了明天的好收成。我们那时候在工地上,都是边干活儿边聊天,讲讲笑话,哈哈一笑,一天也就过去了。”张五银老人说。为了加快工程进度,大家还研究了很多挖渠的好办法。老人站起来比划着说:“我们当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‘鲤鱼大开膛’,先挖最中间,从中间破了土,再慢慢往两边挖。这样的办法不仅省力,担上土还能少走路。而且挖出的水也可以流在中间挖好的渠道里。这也是在不断挖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。”
在多年的水利建设中,河套人民仅凭聪明和智慧研究了很多渠道开挖的好方法,所以才能在缺少机械化的时代,仅凭人力,硬是开挖出一条条渠道,这一条条渠道中流淌着的不仅仅是灌溉田地的水,更是河套人民对生活的希望和盼头。
据张五银老人介绍,“他的祖辈从陕西来到河套地区,最早就是同一代地商王同春一起挖渠的。现在时代好了,有了机械,再也不用人工挖渠了。三盛公把水位抬高,我们自流也能引上水了。我的子女们都在这附近住着,也是农民,我们受过的苦,他们不用受了。”陈为忠老人说,“是啊,现在能按时浇上地了,收成也好了,年轻人们享福了。”
河套灌区记者张蒙/摄
如今,正是收获的季节,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满了黄澄澄的玉米,这便是今年秋天的收成,田地里刚刚结束的秋浇水是来年丰收的希望。
正是一代代河套人民的接续奋斗,才让河套灌区这份千年基业长盛长青,让河套成为祖国北方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。相信,未来它不仅会继续保障这方土地的岁稔年丰,而且会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这就是河套的“80”后,他们用青春、汗水书写治水故事。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故事、讲好他们的故事。
来源:巴彦淖尔日报
文字:通讯员云楚涵(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)
编辑:陈龙校对:希吉乐